【专访】80后:懦弱的一代?失败的一代?
发布时间:2015-07-29
来源:
80后的青春结束得太早 迅速进入萎靡中年
北青艺评:10年前,“80后”这个群体是以一个“叛逆的写作者”的概念进入讨论视野的,今天我们再来谈论“80后”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杨庆祥:10年前谈80后,他们代表了一种叛逆或完全不同的审美趣味,我觉得背后其实是,不仅是中国,也包括整个世界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想象。所以韩寒、春树、张悦然,郭敬明成为一个热点。但是10年以后,那种叛逆的色彩在慢慢弱化,大部分80后在30多岁以后也开始慢慢融入一个生活秩序,甚至是文学秩序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80后,基本就被遮蔽,慢慢再也不能发出声音,可能还有继续留下来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们自己写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阎连科:今天谈到80后不是十年前昨天的80后了。80后这个概念出现是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再说80后,社会学或者文化价值更大一点,远远超出文学的意义了。我们当年说的那些80后的领袖,在文学上开始式微。郭敬明,毫无疑问离文学渐行渐远,韩寒也同样是这样,张悦然作品量也没有以前大,总体受关注的程度在下降。但是,今天谈80后已经远远超过文学的价值,有一代人文化的价值。
张悦然:10前80后主要是一种反叛形象,主要写的是叛逆青春,那时候的80后肯定不需要《80后,怎么办》这本书。但是到了现在,变化非常大。我的问题在于这代人是不是变得太快了一点,好像青春结束得太早了一点,一下子就进入了一种很萎顿的中年的状态里面。正是在这样快速的消失当中,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停下来审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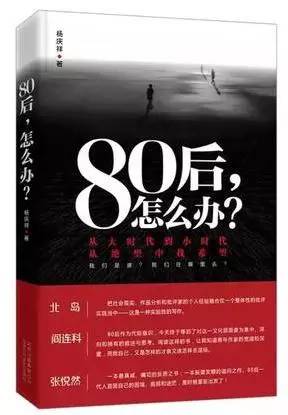
《80后,怎么办》
作者: 杨庆祥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5-6
北青艺评:造成一代人身上“早衰”和“否定性”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呢?
阎连科:就那么几年时间,一代人迅速变得萎靡不振,迅速融入这个社会,迅速认同于这个世界,快得超出人们的想象。
我发现很多人对80后是有一个误判。比如我们在10年前,15年前,说80后这一代人非常反叛,我那时候也觉得是那样。今天想,这代人几乎没有反叛的地方。30年代,鲁迅、郭沫若、巴金们那是真正反叛的一代人,丢掉老婆就丢掉老婆,丢掉孩子就丢掉孩子,说不要家庭就不要,那才是真正的反叛。
49之后,我们发现真正的反叛是我们的爷爷,他们真的是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犹豫,说走就走,甚至说杀人就杀人了。后来再想你们的父亲这一代人,不管是真正的反叛还是假的反叛,他也反叛,他说革命就革命,可以把父亲、母亲揭发出来,上山下乡,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趴着火车就到乡村去了,就到青海、到西藏去了。但是,80后你几乎看不到他们反叛在什么地方。
我们为什么当时对80后会有那么大的希望?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其实都是靠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反叛进步的,当然我们说要靠知识、文化、科学等等那些有头脑的思想家、哲学家引导我们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如果没有下一代人的反叛,社会几乎不可能进步。
第二个误判是,我们曾经认为这代人特别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你今天仔细去想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自我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质上,比如说房子、车子、口红、名包,我想要,我想买,父亲母亲帮着我买,但是找不到他们在精神上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方。
去年看《后会无期》,当时觉得,这个社会有巨大的吸引力,连韩寒这样的人也把那一点自我为中心的精神完全融化掉、吸收掉了,完全像一滴水融入沙漠一样,你不知道这滴水到哪里去了。这滴水滴到大海里你知道它还存在的,但是滴在沙漠里你就知道这滴水已经不存在了。

《后会无期》
相对于50、60,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找不到80后的声音了。80和90的孩子都完整读完大学,但是读过大学为什么出现这么懦弱的一代人?不能说完全没有自主精神,但是没有我们想象那种反叛精神,这些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独立,他们不是独立思考的一代。
看杨庆祥的文章恰恰有这样的感受,你觉得我终于有一个人,他把这一代人的问题集中的进行了梳理和思考,你可以不赞成,你可以反对他,但是这一代人站出来总结他这一代人,尽管里面也有一些观点我不一定那么赞同。
张悦然:我觉得80后这一代人身上本来确实是有一些叛逆的东西,为什么说我们当时写的东西会有那么多的读者,我觉得还是因为有共鸣的。现在回想起来不管韩寒、郭敬明还是当时很多其他作者,真的就是残酷青春的东西,黑色负面蛮消极的东西,我觉得是那代人当时的需要。但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的需要,就是暖男,就是心灵鸡汤,现在如果说还是出来这样的人,叛逆的角色,我还是在写残酷青春,实际上现在的市场已经不需要这样东西了。
为什么阎老师对这一代人寄予那么的大期望,是因为那代人身上肯定带着一个否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很快就被浇灭了。为什么?那么可能《80后怎么办》这本书是杨庆祥作为一个内部的经历者,也是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80后这个群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使他们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使他们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可能锋利的、尖锐的东西,使他们变成了现在温和的,并且妥协的,极其适应体制的一代人。
郭敬明成为偶像 会对这个社会带来巨大危害
北青艺评:在《80后,怎么办》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这一代人的“历史虚无主义”?
阎连科:我是赞成这一点的,50、60年代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历史的参与,有人是被夹裹进去,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参与历史的一个人。但是到这一代人,主动对历史退场。对社会和时代的否定,为什么现在变成一种认同?我觉得这一代人缺少一种最独立的坚持的东西,被这个社会左右,被时代塑造。
杨庆祥:这一代人为什么提不出质疑,只能接受,恰恰相反是50后,甚至像30后、40后提出质疑,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历史关照在里面。我们最大的虚无主义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现存的秩序是天然合理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你有这个历史和没有这个历史,对世界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导致了80后很懦弱的认同现实秩序的重要原因。所以要重塑这些历史,你可能就会建立对社会批判的视角。
我们不敢去追问,会不会有一个另外的可能性或者另外的路、会不会有更好的社会或者更好的秩序?我后来总结了一下,我们,被生活绑架。
北青艺评:谈到80后,郭敬明和韩寒曾经一度成为话题,最近《小时代》上映,又有一拨人开始讨论郭敬明。阎老师是怎么看的?
阎连科:我觉得今天郭敬明的意义,写作的成功失败都不重要。最可怕的意义是今天居然成为中国的一个偶像。我们个人赞成他的努力、他的勤奋,他的经营。但他成为偶像的时候,会对这个社会带来巨大危害。我特别认真看过《小时代3》,我觉得拍这样的电影不稀奇不可怕,看的人太恐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票房,为什么大家一边骂一边要去看。

《小时代3》
前几天还在说郭敬明抄袭的事,这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但有一点,一个人抄袭了,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还得到那么多人的赞赏。当你的偶像没有是非标准,下边的人一片欢呼声,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
杨庆祥:我觉得每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去选择去创造怎么表达他自己。郭敬明的《小时代》电影、小说就是他的表达,这个都无可厚非。我觉得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把这种表达唯一化或者偶像化,或者说我们认为这种表达代表了大部分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它的危害之处。
一个很好的作者,也很难获得我们当年的认可
北青艺评:从文学意义上来谈呢?刚才阎连科老师也提到80后文学整体式微。
杨庆祥:在文学意义上,郭敬明和韩寒根本不值得讨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缺乏最基本文学的意义,比如韩寒,像《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当时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但我认为那是非常糟糕的,非常蹩脚的小说。一些最基本写作都没有入门。它文本所提供出来,没有任何营养,基本上是以他们的这种姿态来拉动他们的文本,以他们社会化的角色。总体而言,10年来,80后这代人的写作无论是在社会影响上面还是内在质地上面都出现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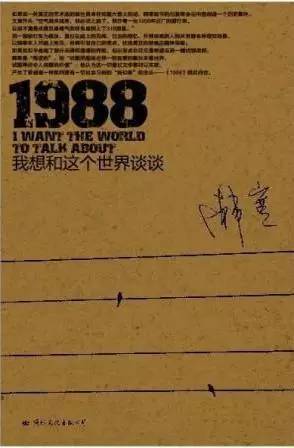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作者: 韩寒
出版社: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0-9
张悦然:我觉得文学读者在减少。某一个很好的作家,我觉得他小说已经写得很好看,但这个好看,也不能够给他带来像我们当年那样的认可。他必须要去参与电影,也要去做别的事情。在西方的话,可以像村上春树,他东西足够好看就好,可是在我们这边,纯文学的东西再好看读者还是觉得费力气,更多读者想要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些网络文学提供的东西,不用思考的那种,其实现在纯文学读者的数量真的是比那时候减少很多,而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读者多?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读者是高中生、是刚上大学。读者现在去哪儿了?早就去考虑房子、孩子、股票各种各样的问题,谁还再读那么费劲的书。
现在就去评估这代人还是很早,我们讨论的是他们之前新出的那些作品,一个新的更成熟的作品可能还需要时间。
杨庆祥: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80后这代人应该沉下来。
阎连科:《捉妖记》垃圾得不可思议

《捉妖记》
北青艺评:最近大热的电影阎老师看吗?
阎连科:我每天下午看电影,最近刚看了《煎饼侠》,卖票的人见我第一面就说,你没带老年证吗?老年证拿出来可以便宜一些。看到《煎饼侠》我就在想,这个电影无论是艺术到拍摄过程,几乎没什么可谈。但是为什么我也喜欢?至少它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恰恰是这一点打动所有观众最柔弱的地方。喜欢煎饼侠的,可以看看《80后,怎么办》,在这本书里,完整的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失败,谁让我们失败?我们以后有可能会怎么着。
《捉妖记》我也看了,今天我一看《捉妖记》票房超过了《泰囧》,我看的时候坐在那儿非常无语,真的是垃圾得不可思议。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最可怕的是从80、90后开始,文化滑下来了。真正给一点点对人、对社会有思考的电影,大家反而不会看。不能简单归咎于没有艺术院线的问题,更要思考的谁把我们这代人引导到这个地方来了。
现在的作品写得越来越漂亮 看了就没劲
北青艺评:书里还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80后是没有青春的一代人。我们稍微扩展一点到现在的文本,青春电影、小说很多,你们觉得有很好的反应这一代人的青春吗?
杨庆祥:如果青春意味着叛逆、挑战秩序,意味着寻找另外的价值观和人生,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是没有真正的青春。
阎连科:我们这一代说青春就是混到城里有饭吃就是青春。电影、小说只是有青春的年龄但没有青春的意义。
杨庆祥:生理性的青春,不是那种文化自觉意义上的青春。有个最直接的对比,你看杨沫当年写了一个小说《青春之歌》,那个时候的青春从那个角度来界定。我们现在你看《致青春》,它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青春。80后的青春还没有找到它合适的表达方式。
张悦然:《麦田守望者》,那也是一代人青春的小说,但是现在美国也没有这样的小说,我觉得现在阅读就是走向更个人化,我们不再想要寻找那样的一个,成为一代人的声音的那样的青春的小说。
北青艺评:我上次跟冯唐聊《万物生长》,我问他青春一定要和时代去互动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阎连科:你看《蒂凡尼的早餐》,一代人一定有共性的东西。
杨庆祥:一个历史感,你可以不写历史,但是你的作品一定要有历史感。历史感不一定要写历史事件,那是历史,你要抓住后面这个东西。
我其实特别警惕80后去写历史,因为很容易成为一种传奇式写作,或者猎奇式写作,你没有办法提出问题。最重要的一些作家,托尔斯泰能提出问题,而这个问题过了十年之后它还能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十年之后,读者不再来读你的作品了?就因为你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时过境迁,这个问题消失了。什么是经典?它的问题能被反复生产,它才能够在不同时代得到回应,这才会成为经典。
张悦然:确实,我们这代人包括我后来看到90后,在技术层面上来说确实比以前的人越来越好,艺术、语言、技术包括阅读,但小说里面所承载的思考,是不是能够有突破。
杨庆祥:所以我一直提倡,更年轻的作家不应该写更娴熟的作品,甚至你要写一些粗糙的东西。因为这种粗糙的东西能够承载能够提出问题,50后那批作家其实是泥沙俱下,但是他们血肉感、生机勃勃,真是有元气,你会发现80后这一批作家越来越没有元气。
张悦然:现在作品写得越来越漂亮。
杨庆祥:看了就没劲。
我们“最中间”但不是“中坚”
北青艺评:怎么办呢?杨庆祥书中说,“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异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这是不是你为同代人开的一个药方?
杨庆祥:昨天看到龙应台的小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她说,这个社会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大部分人都是坐在这个车上,也不看车外,随波逐流,这个车把他带到哪里去就带到哪里去。但是总是有那样一些人,他总是很好奇,一定要伸头,伸出车窗外看看这个车到底往哪里开。如果发现车开得方向好像和他想得不一样,他就喊出来了,这个车开错了,要调整一下。她说这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思考者。这种人越多,这个社会可能会走向一个更好、更高级的社会,如果这种人很少,这个社会就可能非常危险。
实际上我个人作为一个同时代的人,对80后这一代越来越偏激,如果站在2015年的节点上来看,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代的思考者是失败的,我会非常坚决、可能有点刻薄地看我们这代人的状态,就是失败的一代。这个失败不是说此时此刻买不起房子的失败,或者此时此刻找不到工作的失败,不是。这种失败是针对1980年代初我们的父辈,他们对我们充满了期待,我们自己也对自己充满期待,以为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最低的层次上,我们可以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但是在2015年这个节点来看的话,这些全部都失败了。
抵抗有很多的途径,比如你写书或者你生产出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产品,文化产品,也是可以的。从《小时代1》一直到《小时代4》,再到韩寒的《后会无期》,何炅的《栀子花开》,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生是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稍微有一个思考能力和鉴赏力的人都能明白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居然大行其道。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里面,就像张悦然说的, 80后正是社会“最中间”的力量,所以我对80后的一个描述叫做什么?中而不坚,你是在中间,但是你不坚硬,不坚挺,也没有抵抗的力量。什么时候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和这个世界进行对话,如果有方子的话,这就是我想提供的东西,具体的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转自微信公众号:北青艺评
编辑: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