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我院朱冠明教授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8-03-19
来源:朱冠明
简 介:
朱冠明,1973年出生,湖北省公安县人,祖籍安徽凤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94年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获学士学位;1997年、200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分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是汉语词汇语法史和佛教汉语。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2012年获吕叔湘语言学奖一等奖。
访谈人:
于方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赵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5级本科生。

朱冠明: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地处洛阳,业内简称“洛外”,外语方面有一些很好的学者,前一段上央视“朗读者”节目很火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就在洛外工作过。当时军队需要中文人才,所以组建了中文系并在1987年开始招生。我是1990年上大学,是第二批中文本科学员。
在军校除了严格的军事管理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外,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其实同地方大学差不多。给我印象最深、常常让我想起来非常感动的是,几乎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非常尽心尽责,把教学当最高的使命,想方设法替我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包括把一些阅读材料为我们油印成册。因为性格资质方面的原因,我个人对语言类课程更感兴趣一些,当时给我们上语言学方面的课的,有现代汉语的李宗江老师,古代汉语的华星白老师,音韵学的王珏老师,还有教修辞学的刘哲老师、语义学的史金生老师等等。这些老师对我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大二开始教我们古代汉语的华星白教授。
这位华教员(军校习惯称老师为“教员”,称学生为“学员”),和另一位教我们现代文学的周敏老师(周老师在课堂上明确要求我们称其为“老师”,不愿被称为“教员”),是一对伉俪,他们是60年代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和我后来去复旦读硕士、博士时的导师胡奇光先生是同班同学。华教员给我们上了一年的古代汉语课,后来还上了文字学、训诂学。他功底非常好,把一些知识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所以我上他的课非常投入,也愿意花时间。后来的文字学课,华教员要求我们课外读《段注》,给我们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读书的计划,正文总共700多页,每天读7页,一学期的时间恰好能够读完。扎扎实实读下来,当时觉得有点辛苦,但收获确实是挺大的。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对一部“唐诗三百首”新注本的勘误。我找到三百多条错误,觉得该书质量低劣,便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写道(大意):“如此‘新注’,如任其流毒远播,必将贻害后学;且待始皇再世,焚之而后快。”论文指导老师是华教员,他们这一代人可能对这种战斗性的语言十分敏感,专门把我找去谈话,教导我对待学术问题不能打棍子;而且我交给他的毕业论文稿子中也有不少问题,他用红笔一一划出,然后在文末批了四个字:请君入瓮。
出于对华教员的敬仰,我后来读研选择了汉语史专业。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是华星白先生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吸引我走上了汉语史研究这条道路。”今年年初华教员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

1993年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上大三
访谈人:您后来在复旦大学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呢?

朱冠明:
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复旦大学读的。复旦大学语言学很强,名家辈出,同时学术非常自由,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各种思想都能够接受,而且比较前沿,对西方语言学界的最新研究跟进得很快。比如张世禄先生就是最早用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学者之一,也很早就写书介绍布龙菲尔德等西方学者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戴耀晶老师在80年代末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汉语时体问题的,已经充分关注到国外Comrie等学者对时体的分析。杨宁老师在1995年给我们上专业英语课,使用的教材就是John R. Taylor在1989年出版的那本认知语言学名著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语言的范畴化》),要知道90年代初正是认知语言学在国内刚刚开始热起来的时候。
我在复旦的硕士和博士导师都是胡奇光先生,他是做小学史研究的,以一部《中国小学史》而知名。硕士时有一学期是我到胡老师家里,他单独给我上课。他把过去读一些传统语言学著作的几厚本笔记,和一堆一堆的卡片,拿出来给我看。他做小学史,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方方面面都要涉及,而且他自己的主张是从文化史的角度阐释小学的发展演进,所以他关注的面是很广的。他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学生做词汇、文字、音韵、语法都可以,按照你的兴趣来,然后他从宏观的角度在学习方法、研究方法上进行指导。所以他培养的学生,都有各自所长的研究方向――总的当然都是在汉语史的框架里面,细的研究方向却很不一样。我觉得胡老师抓大放小、因材施教的培养模式是很好的,胡老师总共带的学生并不多,大概就十来个博士生,现在大多都还活跃在学术界。
朱冠明:
1999年上半年,李宗江老师请当时在南京大学工作的汪维辉老师到洛外集中讲授训诂学课,我因此有幸结识了汪老师。到复旦读博士的第二年,即2000年秋天,我到南京去拜访汪老师,跟他聊起论文选题,汪老师建议我选做一部佛经。当时学界研究佛经语言已渐成热潮,不过专书研究还并不多。我听从了汪老师的意见,虽然那个时候我对佛经还一点都不了解。
我回复旦以后跟一个读古代文学的同班同学陈开勇(陈允吉先生的学生,现在浙江师大工作)请教。陈允吉先生是做佛教文学的,所以他带的博士生一入学就在他的指导下系统阅读《大正藏》。我问开勇兄:“就你的阅读经验看,哪一部佛经的口语性比较强?”他推荐我看看《摩诃僧祇律》,并说这里面有很多制戒缘由故事,这些故事都很口语化、生活化。我到中文系资料室,从《大正藏》中复印了《摩诃僧祇律》,开始了我的读经生涯。非常幸运的是,那个时候CBETA已经在网上发布了《大正藏》的电子文本,另外网上也有了电子佛教词典,其中收录了台湾的《佛光大辞典》、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十余部佛学词典,这为我阅读佛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从那时起,算是开始了我对佛教汉语的学习和研究。随着时间的加长,对于佛教汉语和汉语史的情况也就越来越熟悉,阅读中发现的相对有价值的语言现象就越来越多。越有发现,就会越有收获感和成就感。这些年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一块,觉得乐在其中。
访谈人:您研究《摩诃僧祇律》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吕叔湘语言学奖,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您写博士论文的心得吗?
朱冠明:
首先,选题很重要。选一个有延展性的、值得长期投入研究的课题,对今后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在这一点上,我很感激汪维辉老师的指点。我觉得佛经材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宝藏,小投入有小收获,大投入有大学问,总之有多少精力投入到里面都不会是研究的尽头。博士论文只是一个学者学术道路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博士论文的选题不能太“小”了。我听说有人选日占时期上海的一份小报来做博士论文,这样的题目虽然可以做出一篇很精致漂亮的论文,但没有太大的“延展性”。
虽然选定了做《摩诃僧祇律》的语言研究,但具体是做词汇,还是做语法,还一直在考虑。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通雅》謰语(即联绵词),是一个传统的训诂学领域的研究。到博士以后,兴趣转到词汇语法史上来。导师对我很了解,认为我对中古汉语、汉语史的情况可能没那么熟悉,建议我做一个相对小一点的问题。
后来确定做情态动词,是我的师兄杨永龙教授的建议。对于我当时的学术基础来讲,这个选题非常好、很适合我做。一方面,当时对于情态的研究,国内做的还不很够,另一方面,情态又涉及到主观化、语法化,与学界关注的热点十分契合。也就是说,既有新的材料,又有比较新的理论支撑。再加上情态动词是个封闭类,数量是有限的,这比散漫地研究各种语法现象,更容易把握一些。
要强调的一点是理论意识很重要。刚才说到,复旦跟西方语言学界是靠得很近的,我在选定博士论文题目后,有意识地读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相关著作,理论性都很强,如Palmer关于情态和情态动词的研究,Bybee等关于语法化包括情态语法化的研究,Sweetser关于语用推理的研究等等。当时国外学界对情态和情态动词的研究,比汉语学界对于助动词的研究要更深入,这些研究为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关于博士论文,我是选择佛经材料为研究对象,并且集中到情态动词上。但如果在学习研读过程中,也仅仅只关注《摩诃僧祇律》,或者只关注魏晋南北朝的佛典,那视野就过于狭窄了。做汉语史的研究,一定要有一个整体观,中古汉语并不是独立的,它从上古而来,又发展到近代、现代。我后来有一次同蒋绍愚先生聊天,蒋先生还十分关切地跟我聊过这个问题,说到以佛经研究为主要对象当然可以,但是视野一定要开阔。这也成为我后来一贯的追求。另外,虽然题目限制了具体研究对象为情态动词,但在读书、搜集材料时,不能只看情态动词,其他都不管。各种有意思的语法现象、词汇现象,我都会做标注、做笔记。这样留下一个印象,下一次碰到了,就会一下子想起来:在哪个地方也有这种语言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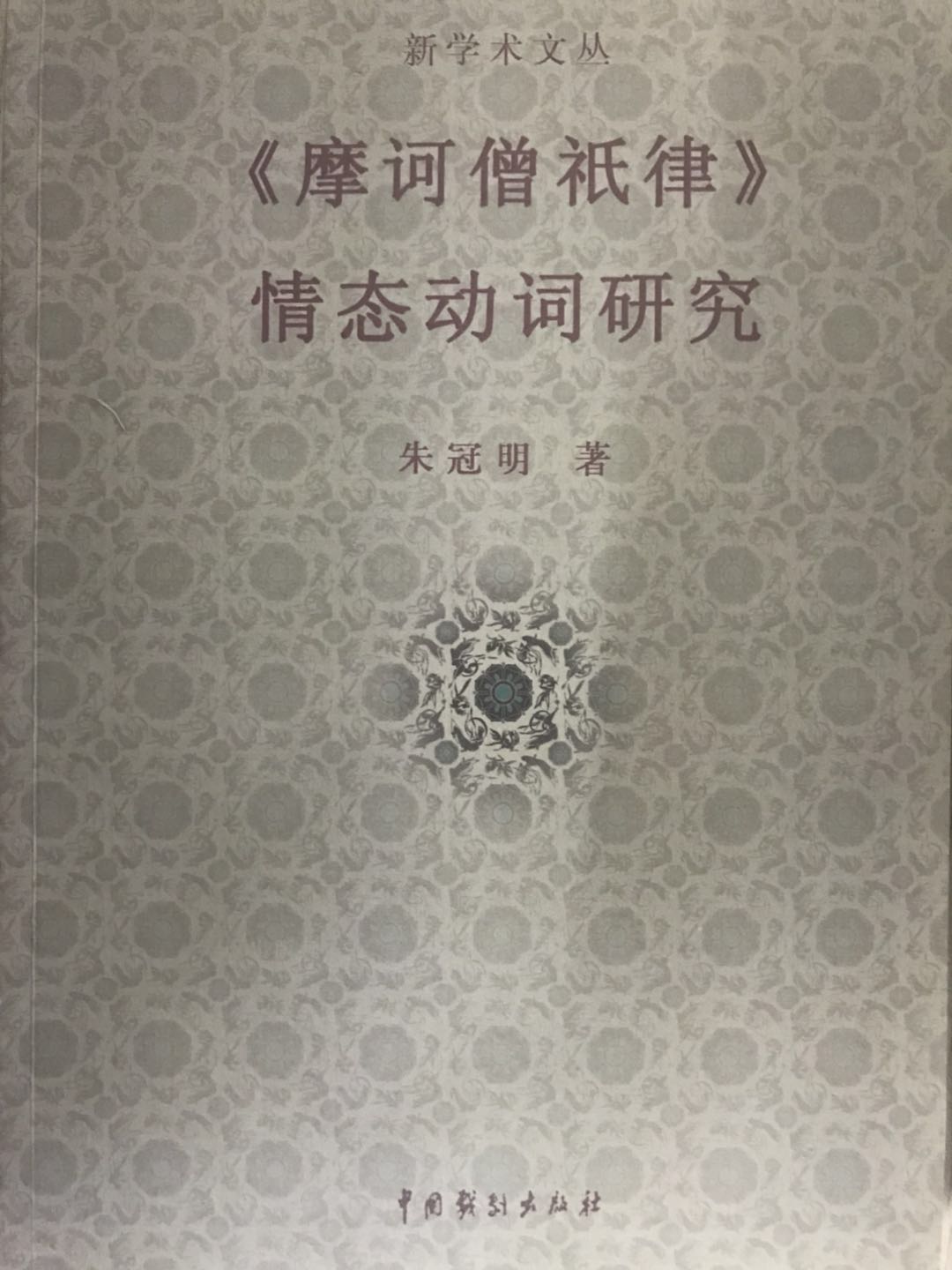
访谈人:也就是说,您在做博士论文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佛经中很多其他的语言现象?这些对您的研究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帮助?

朱冠明:
对。我可以谈两个例子。
一个是关于“自己”这个词。我读《摩诃僧祇律》时,注意到里面“自”有做定语的特殊用法,这在中土文献中不太常见。程工(1999)和董秀芳(2002)都从历史文献角度讨论过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独特性的成因,但都没有谈及“自己”一词的来源和形成过程。我当时跟我的同学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把“自己”的来源讲清楚了,可能以后语法史关于“自己”的陈述都要改写。
但是这个问题留在那儿了,“自”为什么会有特殊用法,如何与“己”凝固成一个复合词,当时讲不清楚。后来我到了北大,学了梵文之后,发现“自”做定语的用法,跟梵语的反身代词sva有关,是受外来语的影响产生的。这就是我2007年发表在《中国语文》上那篇文章《从中古佛经看“自己”的形成》的主要发现。梵语的反身代词sva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做定语,十分自由,这个用法“移植”给了“自”,所以“自”有了做定语的用法。然后,佛经中“自”和本来就可以做定语的“己”同时在定语位置上出现,长期共现于同一个位置,就凝固成一个词。
从最初注意到“自”的特殊用法,到后来写成文章发表,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其间还学习了梵文,我想这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做研究,平时阅读语料文献也好,阅读前人研究也好,问题的发现和材料的积累都十分重要。要做一个有心人,随时记录下有趣的语言现象。我还可以讲一个例子,是我最近刚刚写的一篇文章,在学术会议上交流过,还未正式发表,就是关于“生色”这个词。
“生色”这个词,也是读《摩诃僧祇律》时注意到的。佛制定的戒律中有一条,比丘不能用自己的手去持拿生色、似色,后面跟着的解释是:“生色者,是金也;似色者,是银。”就是说比丘不能用手去触摸金银。当时读了之后,百思不得其解,金为什么叫生色呢?
学习梵文之后,我已经知道,“生色”表示“金”是来自对梵文的仿译:梵文里表示“金”的词有好多个,其中有一个是jātarūpa,jāta是词根√jan(生)的过去被动分词,rūpa是一个名词,意思是形、色。很清楚这就是一个仿译。由此做一篇文章当然可以,但我觉得这只是解决了一个词义来源的问题,有点“小”。
后来有一次,我读到南京师范大学徐复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李贺有一首诗叫《秦宫》,描写家奴秦宫骄奢淫逸的生活,其中有一句“内屋深屏生色画”。关于这里“生色”的解释,众说纷纭,有的说就是“彩色”,有的说是“形象鲜明”,徐复先生认为应该解释为“金色”,形容秦宫内室的金碧辉煌与奢华,这样才更贴切。我一下子想起来以前读到的“生色者,是金也”,这样两个问题就联系起来了。
最近搜集了更多资料,把文章写了出来。“生色”这个词,唐代在非佛文献中,只看到李贺诗那一例,但到了宋代之后,使用就非常多了。宋元明时期,“生色”既用在绘画上,又用在服装的染织上。我现在的结论是:绘画或布料上加金,或者直接用金粉、金丝在画作和布帛上做出金光灿灿的效果,就是“生色”。
在我看来,这样前后贯通的研究,比起简单地解释为什么“金”叫“生色”,更好玩、更有意思一些。如果当时只是看到《摩诃僧祇律》中的“生色”,找到其梵文来源,没有看到徐复先生对于李贺诗歌的解释,可能就写不出这个文章。如果我只看到徐复先生那篇文章——我想很多人也都看到过,因为这一则内容徐复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都有提及——没有《摩诃僧祇律》中“生色者,是金也”的印象,也无法很好地解释其来源。这也是我通过长期积累而做一项小研究的例子。
访谈人:您博士毕业后到北大做了一期博士后,继续佛经语言的学习,我印象中您是在北大学习的梵语?

朱冠明:
在复旦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读到朱庆之老师一些佛教汉语研究方面的文章,他那时已经开始倡导梵汉对勘的研究方法。我认识到这个方法对于佛教汉语研究很重要,也感觉到一些现象可能要从梵汉对勘的角度来解释。当时复旦大学的钱文忠老师也开了梵文课,我去听过几次,但由于时间关系,并没能坚持学下来。
2001年下半年,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一次中古汉语研究会议上,我遇到了朱庆之老师,提出想跟他做博士后,朱老师鼓励我试试。当时我的身份还是军校教师,在时任我们系主任的李宗江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之下,我幸运地获得了到北大做博士后的机会。
在北大做博士后期间,我投入了不少时间,跟着东语系的段晴老师学梵文,上了一学期的基础梵文课,又读了一学期的《法华经》,这样对古典梵语和佛教梵语都有了一些最初步的了解,开始尝试着在研究中使用一些梵汉对勘的材料。
此外我还听了蒋绍愚、陆俭明、王洪君、朱庆之等老师的课,总的感觉是在北大的两年多时间非常有收获。现在想想当时自己还算是挺用功的,常常看着看着书,就“不知东方之既白”。
访谈人: 2007年您到人大来任教,基于什么原因您又到社科院做了第二期博士后?这段经历又给您带来一些什么影响呢?
朱冠明:
社科院语言所和北大在语言学上都很强,但风格还是不太一样。在汉语史的研究上,相对来说,社科院更加注重与现代语言学的结合。我的联系导师吴福祥先生,他对西方语言学界相关领域研究的熟悉程度之高,令人叹服。他的研究大概在2000年前后有个分界,之前做专书语法研究,文献材料做得很细致;2000年以后,吴老师不仅理论意识非常强,而且在语法化、方言历史语法、民族语言、类型学等多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另外,社科院很多老师都是各自领域中非常好的学者,我觉得如能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对今后的学术成长会有很大帮助。
我在社科院待了将近三年。当时一边在人大教课,一边去听社科院的课程。吴福祥老师的“形态句法学”、刘丹青老师的“语言类型学”、张伯江老师的“功能语法”、方梅老师的“篇章语法”、沈明老师的“语音训练”等等,我都坚持听下来了,这些课程对我现代理论素养的培养帮助很大。
社科院、北大或者复旦,这些单位语言学都比较强,在学术风格上有共性,也有个性。不同的地方待一待,古人说“转益多师”,这对个人成长确实有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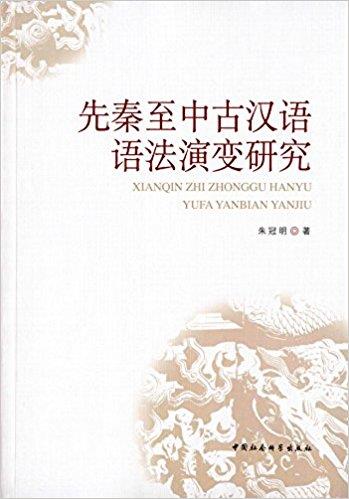
访谈人:您一再提到现代语言学理论素养,就我们的理解,其实主要是指对现代西方语言理论的学习和借鉴吸收。请问您有过国外学习的经历吗?

朱冠明:
我只短期在国外待过,2013年年初,受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UCSB)遇笑容教授的邀请,我在那儿访学了三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学期,即美国大学的冬季学期。我完整地旁听并参与了语言学系和东亚系的一些课程,对美国高校体制、运行机制和课程设制及授课情况,有了切身体验和初步的了解。印象深刻的有几点:
一是他们的语言学系规模不大,在职教师只有十几位,但实力却很强,尤其在功能语法、类型学方面,国际上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原因在于有一批世界级的学者,如已退休的有Wallace Chafe, Sandra A. Thompson, 李讷(Charles N. Li)等,在职的有Bernard Comrie, Marianne Mithun, John W. Du Bois等,这些学者都鼎鼎大名,估计你们听起来也不陌生。
二是非常重视对学生田野调查能力的培养。我在的那个学期,至少有三门课直接与这方面的内容相关。Mithun开了一门田野调查课(Linguistics: Field Methods),在语音实验室上,要进行听音记音训练;一位叫Robert Kennedy的年轻老师开了一门语言分析课(Linguistic Analysis),训练学生通过一大堆相关的语言材料来分析某种陌生语言的形态句法;还有一位上句法学课的老师,刚刚从马来西亚做完调查回来,课堂内容主要就是讲授她对当地某个土著语言的调查与分析。
三是他们开设的课程很丰富,但每个学生每学期选的专业课却不多,因为每门课都有大量的课外阅读文献,也有定期的作业和测试,如超过三门课学起来就会很吃力。不像我们这边,为完成规定的学分,研究生每学期要学七、八门专业课,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每门课都不可能学好,这种情况亟待改进。
尽管我在UCSB只待了三个月,在专业上也觉得挺有收获的。像刚才提到的Kennedy开的那门语言分析课,我全程参与了,觉得这种训练对提高自己分析语言的能力非常有帮助。顺便提一句,由吴福祥老师和我主持翻译的Thomas E. Payne的《探索语言结构》(Exploring Language Structure)一书,译稿已交出版社,年内可能会出版,此书每章后都有大量的练习题,就是训练这种语言分析的能力。另外我还听了Comrie教授的两门课,一门是给本科生开的句法学,所用的教材就是刚才说的Payne这本书;另一门是给研究生开的语言类型学,Comrie是这个领域顶级的学者。我后来做了一项研究,探讨近代汉语中一种无标记的关系小句,最初的想法就是在Comrie的课堂上产生的,写作过程中也同Comrie进行了交流,他还寄给我尚未出版的书稿中的相关部分。
我个人强烈建议有条件去海外交流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去交流一下,无论是长期读学位,还是短期交流,都行。这对增长见识、增进对海外学术界的了解以及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都有好处。
访谈人:最后还是回到您的研究方向上来。能不能请您谈谈对佛经语言研究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些看法?

朱冠明:
佛经作为一种价值很高的语言材料,值得挖掘的东西还很多。我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古译经中的“未曾有”及其流传》,其中提出佛经翻译给汉语带来大量的新词,有些已经完全融入汉语,成为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如“劫”“魔”“世界”“因缘”等;有些只在译经中出现,其他文献中并不使用,对汉语没有发生影响,如“因陀罗”“波罗夷”“沟港”“善来”等;还有一些词介于二者之间,它们在译经中高频使用,但译经之外多见于涉佛文献和书面语,口语中少见,尚未彻底汉化,该文讨论的“未曾有”就是这一类的典型,前面提到的“生色”也大体属于这一类,其他如“羯磨”“般若”“具寿”“有情”等都是。以往研究的重点在“劫”这一类,而对“未曾有”这一类关注不够。梁晓虹教授曾在聊天时跟我说到,佛经语言这个宝藏,露在地面的“宝贝”(大概指“劫”这一类)差不多已被她们这一辈的学者像扫落叶一样扫光了,剩下的就需要往地下深挖了。而我觉得“剩下的宝贝”,如“未曾有”这一类,其实埋藏得也不深,稍稍“排沙简金”,即可“往往见宝”。
在研究方法上,这些年的研究实践证明,朱庆之、辛岛静志等先生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梵汉对勘的确是一个利器。因为汉译佛典确实是从梵文等原典语言翻译过来的,不从对勘角度,有些东西是讲不清楚的。现在年轻一代的学者,比早年有更多便利的条件来学习梵文,据我了解,除了北大外,社科院、人大、复旦、浙大、川大等都在开设梵文课。现在中古汉语或汉文佛典的学术会议,每次都能看到一些年轻学者使用梵汉对勘来进行研究。另外,朱庆之老师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是那个梵汉对勘的语料库,现在公布的有《法华经》《维摩诘经》《俱舍论》三部佛经,逐字逐句的梵汉对勘,且对每一个梵文词都进行了详细的语法标注,在香港教育大学的网站上免费供大家使用。有了这个语料库,即便不懂梵文的人,也可以在研究中使用梵汉对勘材料。
另一个方法现在做的还很不够,就是同经异译的对比研究。注意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人不算少,但目前真正见到的使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词汇、语法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成果,还不多。
专门从事佛典汉语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景非常看好。这是一个国际性很高的研究领域。日本学者之外,国际上做佛教研究的,过去除少数学者如许理和(Erik Zürcher)等之外,其他人更关注梵文佛典而比较忽视汉文佛典,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他们读不太懂汉文佛典。但现在有些学者,比如辛岛静志,汉文很好,同时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等原典语言也很好,因此在汉文佛典研究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当前国际上研究汉文佛典的学者越来越多,比如梅维恒(Victor H. Mair)、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梅思德(Barbara Meisterernst)、那体慧(Jan Nattier)、Paul Harrison, Jonathan Silk, Max Deeg, Christoph Anderl, Daniel Boucher等等,不过他们不一定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召开11届,最近几届2015年在日本召开,201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在台湾,2018年已定到韩国——在中日韩等北传佛教的地域,有很多学者在从事汉文佛典语言的研究,相信以后欧美学界也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


